|
俗话说,“一白遮百丑”。有时候,“白”也不失为一种审美标90准。
白色,是一种纯洁的、静谧的颜色,它不惊扰他人,在温柔中透着灵秀之美。

享有世界声誉的中国颜色,除了“中国红”,还有一种“中国白”,法国人称为Blanc de Chine,用来指代中国的德化白瓷。
中国白,是纯粹之中的万有。白的传统,自邢窑、定窑开始,不失端庄凝重,又仿佛有仙气浮动。还有永乐的白瓷,人们起了个名字叫“甜白”,用一个巧妙的称呼,完成了从视觉、味觉到心灵感受的全方位抚慰。
中国的白,白如雪,润如玉,透如绢,如美人肌肤一般白净,如夏日早晨一样甜蜜而清凉,白得刚刚好,白得无法更完美。


据统计,《诗经》里提到白色范畴的词,频率最高,共四十三次。
“皎皎白驹,在彼空谷。”在晨曦的绿野上,骑着白马徐徐走来的,正是谦谦的君子。“月出皓兮,佼人兮。”明眸皓齿、肌肤胜雪的女子,才能称得上是美人。
受先人偏爱的白色,有庄严、典雅、静穆的美感,也有柔和、恬淡、朦胧的意味。

白色,有纯洁、无暇的寓意,但是又太过简单和朴素了。
在中国文化里,白色有时会被定义为不吉利的颜色。白并非越白越好。绝对的白度,外露而刺眼,给人带来的观感,是冰冷的惨白和死白。
中国人喜欢的白,不是抽象的白。中国人眼里的白,可以是很多具体的事物:是银,是雪,是美人的牙齿,是海边的贝壳,是柔和的月色,是明亮的日光……
中国人欣赏的白,是“不纯正”的白。这种白,在本色里注入了融融的暖意,在无色中萌动着浪漫生机。

白色,是无色之色。然而,当匠人的手工,遇到了自然的造化,最空洞的白色也生出了多种可能,带来丰富的联想。
明代的德化白瓷珍品,在相同的瓷质里,烧出了不同的瓷色:象牙白,细腻温润,在乳白之中微闪黄色;猪油白,油光明亮,质地坚实,白润如油脂;葱根白,纯白洁净,却略带了一些青;孩儿红,像婴儿的皮肤,在洁白莹润的表面之下,粉嫩透红……
白,是平等的对话。白色,被赋予了象牙的高贵,也有猪油的平凡。每一种白,都在“无中生有”的底色上,显露着天然的微妙。无论有多少种白,都是需要人的想象力来配合的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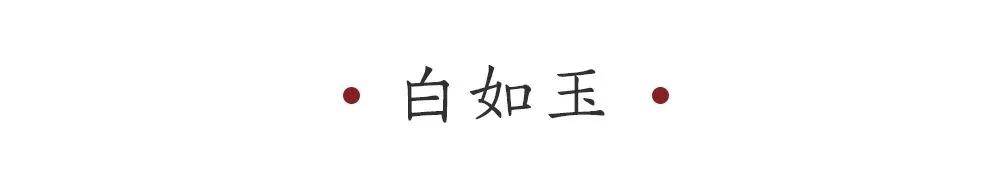
庄子说,“朴素而天下莫能与之争美。”中国白,以质取胜,而非以色夺目。
正因如此,每一片瓷上,都映着“玉”的影子。中国人的心中,始终解不开玉的心结。直至今天,人们赞叹瓷器的釉质好,最常用的赞语仍然是“温润如玉”。

中国把“玉”作为美的理学。玉的美,是“绚烂至极归于平淡”的美。可以说,中国一切艺术的美,以至于人格的美,都趋向于玉的美:内部有光彩,但是含蓄的光彩,这种光彩极绚烂,又极平淡。
白是极致的朴素,而在极致的朴素中,又有无限的神采。当瓷变得冰清玉洁,就不仅具备形色之美,也有了德行和精神。

白瓷如白玉。它不追求纯粹的白,不追求无瑕的白。它追求类玉、类白,追求君子之德,追求简单中的丰富。
邢窑的白,像蓬松的雪。定窑的白,似轻薄的绢。元代的白瓷,如鸭蛋白中泛青,谓之“卵白”;永乐的白瓷,白如凝脂,恬静柔润,称为“甜白”;嘉靖的白瓷,纯净无杂;万历的白瓷,透亮明快。一样白色,各种面貌,不胜枚举。
不同的白,像不同的人生,可能表面无奇,慢慢品味,才能发现有粗有细,各有痕迹。没有一种白是千篇一律的。它们看似平淡,却从来没有失去质感。

白,不能藏垢,哪怕最轻微的杂质,也会丝毫毕现。白,又最能容纳,衬着不同的纹理、光色,令鲜活的气息,带来更由衷的喜悦。
宋代出现了青白瓷,在恬淡的白中隐隐泛着青,像被风和水滋润了的好心情。平淡素洁的青白色,有君子的风度,有清淡的意境。它不只有一种物性,而更渗透了淡泊、虚静的人性。
那些灵动之气,至今仍流淌在莹润的釉水上,在以白为底的世界里,渲染出柔和悦目、温润恬静的美感。

对白色的爱,是对生活的讲究。这种讲究,是一种臻于极致的精致,化为“素”的展示。在白色上铺陈开来的,是一览无余的交代,是浩瀚无边的胸怀。
白,有自己无色的主张。它因单纯而严谨,因严谨而优雅,因优雅而自信。白在瓷上,有章法,有包容:在审美情趣上捕捉均匀的质感,而不是颠覆;把生活布置得朴素,非大自信不足以言之。

白,既有中国人丰富和诗意的表达,也曾是东西方交流史上的代表性符号之一。“中国白”,不只关乎于材质,也关乎于审美,同样还关乎于时间、地域、族群、情感。
在色彩缤纷的世界里,放置一抹白,反因它的沉静寥落,而格外跳脱。中国的白,用最不刺激的方式,做着涤荡心灵的征服。它就是这么不可思议,用最朴素的样子,引诱世界。

中国的白,从诗经里走来,再映照在瓷上,一直在提醒着我们:最为纯粹的,也最是深情。
白给我们带来的,内心的感受,多于眼睛的摄取。它无需过分的装点,只是独立的表现,像喧嚣中隐约的回响,在时空里诉说着悠远的情怀。
宁静的中国白,在自在中沉淀下心绪,在孤独中承载了一切,如日常的淳朴,如参禅的玄幽,见微知著,绝尘脱俗。
(责任编辑:zgshw) |
